
费正清解剖中国问题的“决定性因素”
费正清是美国很有影响的汉学家,他的作品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,一点都不陌生。
除了他的“中国问题专家”身份外,其作品也常常以“海外比较”的视野让人耳目一新,不管是他的《伟大的中国革命》《中国:传统与变迁》《美国与中国》,还是最近被翻译出版的《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》,都是如此。透过书名中的“与”字,我们可以发现费正清对“比较”的天然兴趣。
费正清的作品看起来有味道,要么透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,要么透过学科的交汇,要么透过国别的比较,让单一的叙述变得形象生动,变得跌宕起伏。
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作出重要贡献
《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》一书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,一出版就受到广泛认可,被视为费正清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而作出的“重要贡献”(傅高义语)。为什么说此书的出版对理解中国对外关系有着重要贡献呢?在之前,美国学者对中国对外关系的理解一直存在某种天生的偏见,认为中国乃“稻田”文明,贸易与外交,从来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。这里除了彼此封闭的认识外,当然也有中国本身固有的政治秩序的影响,中国于1842年开埠通商,虽然原有的贸易体系开始崩溃,朝贡制度进一步瓦解,但不管从统治者层面,还是底层民众,中央天朝的心态一定程度上从未褪色,甚至在面对外来侵略时,这种天朝心态愈发膨胀,以至于成了枪炮的直接牺牲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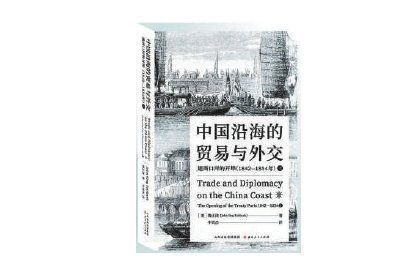
《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》,费正清著,牛贯杰译,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《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》主要讲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贸易制度与外交格局,以及鸦片战争后中国贸易与外交政策的应对、实施、近代重组构建等。这其中,既有历史无奈的剧烈疼痛,也有制度冲突、历史潮流涌动带来的欢愉。在费正清看来,中国长期以来对贸易的漠视,除了本身重农抑商的思想外,还跟朝贡制度以及“夷”的外交认识紧密相关。但事实上,二者又存在悖论。早期,中国与亚洲、欧洲的贸易已普遍发生,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辟,更使得贸易异常活跃。但贸易大多以“贡物”而为,交易的价值无法得到重视。这是因为在朝贡体制下,中国统治者重视的是贸易朝贡的道德价值,或者说政治价值。但到了近代,贸易本身凝聚的物质价值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一方面要维护传统意义上贸易朝贡价值,另一方面又要瓦解这种价值,反向凸显贸易的交易价值。这大概就是近代贸易体系的艰难时刻,当然也是其最悲痛的时刻。费正清把这种矛盾展示出来,把悲痛与冲突放在历史的洪流中,读来让人感受深刻。
看似在叙述贸易与外交,实则在解剖中国问题的“决定性因素”
费正清在书中的这种矛盾化的历史建构,大概源于他具有问题意识的历史思考。19世纪中期的中国,在面对着朝贡制度的瓦解,面对枪炮的冲突。其问题根源是什么呢?在费正清看来,帝国主义并非是凌驾于本国人民之上的主宰力量,本国的内部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,在贸易与外交方面显得尤其突出。在鸦片战争中,是主张强硬应对,还是议和,统治者自己都没了主意,在“剿”“抚”两端徘徊,民众更是袖手旁观,这也是必然的,是封建政治制度腐朽、没落的集中体现。费正清把这些问题隐藏在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的叙述中,看似在叙述特定的贸易与外交,但其实是在解剖近代中国道路的发端,解剖中国问题的“决定性因素”。
当然,这种问题意识也不是费正清的独有发现,中国学者在思考近代中国变革时,也大多从历史的潮流出发,从政治制度的世界变革洪流中去考察。但费正清显然是比较高超的一位。这里有他特定的视角,以及驾驭、融会贸易与外交关系的能力。《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》将贸易与外交融合在一起:贸易势必有外交,外交也必然有贸易,二者密切相关。在近代中国,贸易虽然是被迫进行的,但鸦片战争前,中国沿海的贸易兴起是不争的事实。在这其中,贸易催生了外交。在贸易的推动下,尤其经过鸦片战争的冲击,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制度开始缓慢建立。这过程是悲痛的,但也不得不去适应,去建构。
《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》作为学术著作,其中有些认识或许有待商榷,比如认为鸦片战争不仅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“朝贡体系”,而且随着《南京条约》等条约的签署,条约体系开始复苏。所谓的“条约体系”显然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,是我们需要警惕和批判的。但就《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》一书总体的叙述而言,费正清在矛盾中书写,向历史问题叩问,这些都让读者有了亲临历史现场的感觉,加上他的学科交叉、融会贯通的叙述本事,都让人读来意犹未尽。
下一篇:没有了
